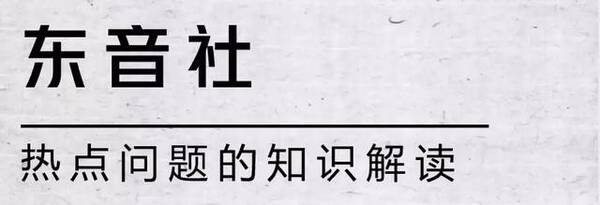
中国有古老的文明,有当代的最优实践,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。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。
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。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,解释自己。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,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。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: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,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,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。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?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,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,西方社会学家,西方政治学家,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,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。结果呢?大家越说越糊涂,越解释越不清楚。当然,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,搞知识层面的“自主创新”。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画,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。

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?简单地说,这是一种思维、思想“被殖民”的状态。从“五四运动”以来,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。进入近代以来,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。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,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,即所谓的向“西方寻求真理”。西方就是真理,就是科学,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。学习西方,便是政治上的正确。在这一点上,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,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,或者象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。总体上说,自由派学欧美,左派学苏俄。很显然,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,都是西方的产物。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,也有类似于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的思想意识运动,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,而不是中国。视西方为真理,为科学,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“非真理”,“非科学”了。长期以来,知识界那些追求“非西方”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“不正确”。
马克思曾经强调过,哲学家有两件任务,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。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。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,但在中国,知识分子人人都想改造世界。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,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。结果呢?越改造,这个世界就越糟糕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,决策者要负责,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。
一个文明,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,就不可能变得强大。自近代以来,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。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。正因为如此,其有能力解释自身,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。实践是开放的,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,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。在国际舞台上,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。
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。社会科学中的“西方中心论”成为必然。“西方中心论”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,其本身并没有错。当人们说“社会科学”时,这里的主体是社会,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。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。然后,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,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意识形态、文化、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。
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,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。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,而不是他人的责任。不过,很显然,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“被殖民”状态下,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。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,首先要意识到“被殖民”这一点,然后,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。
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,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。也很显然,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,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。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。更重要的是,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,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。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,中国可以应用,但不会创新。一个严酷的现实是,一旦涉及到创新,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,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。抄袭知识、复制知识,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。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。实际上,知识和知识的实践(制造业)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,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。

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。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,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。秦朝统一中国之前,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,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。但是,秦朝统一中国之后,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。数千年里,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,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,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。而在近代“向西方寻求真理”以来,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,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。无论是哪一种依附,本质是一样的,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。而对统治者来说,相比之下,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。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,尽管保守,但为社会所接受,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。而后者呢,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,既不能解释现实,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,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。
就是说,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,而是控制。举例来说,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,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,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,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、来做研究,这样才会有创新。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,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,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。为了生存,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(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)申请资金。实际上,即使申请到了基金,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,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。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,而是为了控制。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,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,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。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,而仅仅是控制机制。对掌管金钱者而言,你要向我申请资金,你就必须听我的,我叫你做什么,你就做什么。你越听话,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。当然,你越听话,表明控制就越有效。
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“殖民”体制,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。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,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。例如,在这一体制下,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,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,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,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,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。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,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“研究成果”。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“外国技术,中国原料”的生产过程。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、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。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,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,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。
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,思想就不再是思想;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,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,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,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。这里的逻辑就是:国家越富有,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,思想就越贫乏,文明就越衰落。这是中国的现状。今天,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,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?现实是,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,那么创新便是空谈,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。


 红包分享
红包分享 钱包管理
钱包管理


